2013-02期●人物●
忆英文版《南京大屠杀》著者张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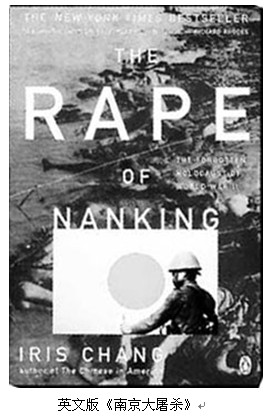

张纯如——一个东西方文史学界陌生的名字,随着英文版《南京大屠杀》的出版与畅销,更随着她谜一样的自杀身亡,这个名字已为公众耳熟能详。我自1995年在南京初识纯如,此后又多次在美国相见,“南京大屠杀”这一纽带,将我们的思想与友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南京安排纯如调查
1995年6月,我接到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著名专家吴天威教授的来信,称最近将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小姐来南京调查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她准备用英文写作一本向西方公众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著作,请我给予协助,具体要求是:安排熟悉相关资料的学者与英语翻译各一人,随张调查;安排采访幸存者若干人,参观相关遗址若干处。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投身南京大屠杀研究后,已决定将此作为自己终身不渝的事业,对于吴教授的请求,当然欣然允诺。我分别约请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先生和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先生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王熟悉南京大屠杀史实,并能阅读日文资料;杨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7月23日下午,我与王卫星、杨夏鸣两位先生在上海路西苑宾馆同远道而来的张纯如小姐见了面。当年她27岁,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双大大的眼睛,能与我们用汉语作简单的交谈,基本不认识汉字。她告诉我们:这次她由美国乘飞机飞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来到南京。1937年时,她的外祖父就在南京做教师,曾经目睹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来在南京城陷前逃到了宜兴。一年前(1994年),她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那些血淋淋的资料,唤起了她对祖辈在南京遭遇的记忆。她暗下决心,要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实当作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这次到南京来,就是为了践行自己的这一心愿,用一部英文著作来向西方社会揭示南京大屠杀这一被遗忘的洗劫。在这次见面中,我请卫星先生负责向她介绍并帮助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夏鸣先生为她作翻译。她对于安排了这样两位有造诣的学者来帮助她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7月25日,我们陪同纯如去南京大屠杀遗址作调查。除夏鸣作翻译外,我还特地约请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段副馆长,来为她介绍各处遗址的历史背景。这一天,纯如穿着宽松的T恤、短裤与白球鞋,看上去特别有精神和充满朝气。我们包租了一辆小车,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东郊、普德寺等南京大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在这些地方被屠杀和埋葬的同胞就达16万余人。每到一地,纯如都用她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将纪念碑与附近的景物,以及我们的介绍,认真地加以记录。从她沉重的表情上,看得出,这一桩桩屠杀暴行,在她的心灵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草鞋峡屠杀遗址,纯如问我:“日本军队在这里一次屠杀了5.7万余人,为什么没有人进行反抗?”我说:“他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曾经徒手去抢夺日军的武器,并造成了少数日军的伤亡。但是,在身体被捆绑和血腥恐怖的气氛中,要进行有效的反抗,也是困难的。”她默默地点点头,表示了对此的理解。
此后,纯如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在卫星、夏鸣和段馆长的协助下,调查、搜集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拜访了朱成山馆长,访问了10几位幸存者。采访中,纯如进行全程录像,并对幸存者身上的伤疤拍了特写镜头。日本侵略军给予这些幸存者家庭及本人毁灭性的伤害,使他们长期生活在惨痛记忆中。她后来在书中写道:“我得知大屠杀期间,其中一些幸存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致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我所见到的情况,令我震惊和沮丧”。
8月10日,纯如于离宁前夕举行晚宴,招待我与卫星、夏鸣先生、段馆长,还请来了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著者徐志耕先生。她表示,由于大家的热心帮助,她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南京的调查、采访和搜集资料的工作,返美后,将尽快投入写作。餐后,她又就调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向我询问,如: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遇难人数的求证、南京人民在屠杀中的抗争等等。我一一作了阐述。纯如在工作中的执着、专注与投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与纯如多次相遇
说来也巧,在南京接待纯如之后大约一个月,我应邀赴纽约出席“对日抗战胜利50周年国际研讨会”。我向大会作了《日本军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报告,后来又先后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讲演。9月20日,我邀纯如到我女儿的住地洛杉矶帕萨迪纳(Pasadena)家中来作客。这一次会面,由我女儿孙路当翻译,因此交流非常充分。她告诉我,返美后,她便夜以继日地整理在南京搜集的各种资料。她还将一些不太清楚的史实提出来,由我一一作答。她说,再过两年,便是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60周年了,她一定要用自己的《南京大屠杀》著作,来纪念这个日子。我说,我也正主持着一个同名的国家课题,并且也要争取在1997年12月之前问世。临行前,她将自己精心查找、翻印的1000多页美国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送给我,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年9月解密的部分日本外交文件、东京审判的部分速记录等。与此同时,她还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寄去了一份同样内容和数量的复印资料。纯如说,她发现在江东门纪念馆中,很少见到西方的资料文献,而如果屠杀发生地的博物馆居然没有这些文献,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我对她这一无私慷慨的举动深为感动。她的《南京大屠杀》著作尚未出版,她就将自己艰辛获得的宝贵资料与他人分享,这真是一种十分高尚的学术品格。这些资料,为我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钥匙。
1996年12月上旬,我应邀赴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出席“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第二届年会”。会议期间,我又一次见到了纯如。她与史维会的丁元先生共同担任会议开幕式的主持人。他们分别用流利的英语和汉语,发表了关于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精辟见解,猛烈回击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对中国侵略和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谬论。
1996年纯如在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查阅南京大屠杀资料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发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一些资料,还打听到了拉贝的外甥女莱因哈特仍然健在。她与莱因哈特联系后,得知拉贝曾写给希特勒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并有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我与纯如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开会见面时,她兴奋地告诉我,将于12月12日去纽约出席一场关于发现拉贝日记的新闻发布会。我说:“拉贝日记的发现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您,是这一伟大发现的核心人物。”她回答说:“在这件事情上,莱因哈特夫人和北美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首任会长邵子平先生才是关键性的人物,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邵子平先生曾在德国留学,在帮助纯如寻找拉贝下落及与其亲属沟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纽约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轰动。
在斯坦福大学会议期间,纯如还同我谈起《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进度。她说,初稿已基本完成,但是还想增加两章,分别写幸存者的命运和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我鼓励她说:“这两章加得好,这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延伸,幸存者的命运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造成的,只有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类的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世界的和平才有保证。”她表示,一定要努力写好这两章。后来,该书正式出版时,果然增加了饱含感情的“幸存者的命运”章与极富政论哲理的“二次劫难”。这样的架构,使该书的内容更臻完整。
2000年3月上旬,我应邀赴旧金山出席“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与纯如再次在大洋彼岸见面。此时的纯如,已经由于《南京大屠杀》的问世与热销,成为国际名人。该书的英、中文版,于1997年11、12月差不多同时出版。其英文版在首发式上被抢购一空。此后,这本书连续10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都排名在前15位。我告诉她,中国大陆的众多报刊报道了英文版《南京大屠杀》在北美热销和她坚决拒绝在出日文版时作任何变动的态度,人们都称赞她是一名“勇敢的斗士”。我还告诉她:我发现,由于《南京大屠杀》的成功发行,在美国校园里关注这一事件的群体,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华人、华裔的狭小圈子里,许多美洲、欧洲、非洲的青年人,都参加了进来。这一段以前不为西方世界重视的历史事件,已经引起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普遍关注。纯如听到我的介绍后,感到十分高兴。她诚恳地说:“我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你和许多中国朋友的热心帮助。”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纯如分在同一个小组,纯如是会议的特邀评论人。这次分组讨论会,是我与纯如相识、接触过程中,唯一一次同台各自讲述自己学术观点的交流。然而,不幸的是,这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令人不敢相信的噩耗
2004年11月9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智慧、纯朴、执着的纯如在这天早晨,在自己白色的轿车内,用手枪结束了自己36岁年轻的生命。长期以来,她一直忍受着抑郁症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煎熬,最终选择了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她还在一封信中,请求人们记住生病以前的她,那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献身于事业的她。
我得到这一噩耗是在11月11日上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十分震惊。在我的印象中,纯如落落大方,善于同人交流,又事业有成,似乎不该得抑郁症,更不该走上这条不归路。此时此刻,纯如当年只身来到南京调查、考察的情景;我们在洛杉矶共进午餐的情景;我们同台作学术报告与学术评论的情景……一下子全都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我无法相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匆匆离去。
这一天,我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对纯如的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11月12日《现代快报》以“《拉贝日记》发现者在美中弹身亡”的大字标题,配发了纯如的大幅照片,刊登了对我的采访报道:
张纯如女士去世的消息昨天传到国内,使南京大屠杀研究学界为之震惊,权威学者孙宅巍指出,她是发现南京大屠杀核心资料《拉贝日记》的关键人物,她的英文著作第一次让欧美人士翔实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对揭露日军暴行有重要意义。
像纯如这样一个活跃、开朗、对生命充满热情的女性,为什么竟会罹患抑郁症,并最终导致自杀?人们善意地猜测:是南京大屠杀的血腥事实,使她的心灵承受不住?是她正着手搜集的二战中菲律宾巴丹半岛美军战俘遭受虐待的残酷事实,使她的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是英文版《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她不断收到被怀疑是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吓信件和电话,使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从逻辑上来说,这些推论与猜测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在她的回忆录与接受采访中,并未正面回应上述这些推测。她说:对于纯如自杀,“这个问题我们问自己问了不知多少遍,但是找不到答案”。纯如之死,给社会公众留下了太多的悬念。
也许,纯如预感到自己会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来从事写作。她于1996年出版了生平第一部著作《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1997年出版了第二部著作《南京大屠杀》,2003年第三部著作《美国华人:口述历史》问世,接着又着手写作以二战中巴丹半岛美军战俘受虐为主题的第四部著作。她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回忆,纯如常说:“生命将消逝,但书和文字可以流传。”“文字是留住灵魂的唯一方式。”“书是写作者实现永生的终极方式。”张盈盈教授《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以一句名人名言作为结束语:“有些人的一生是专为别人而度过的。”真是说得太好了,纯如短暂的一生,正是为了替千千万万冤死的生命寻求公道与正义而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