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期●《改革开放30年》征文选登●
在史学领域里艰辛探索的勇者
—— 访著名多点视角历史学家朱子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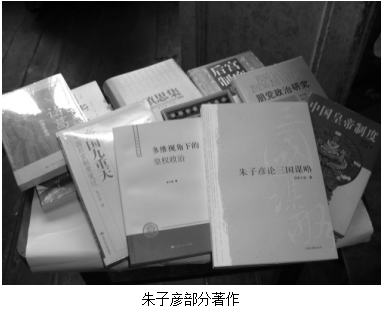
与朱子彦教授煮茗而谈,感悟颇深:他虽身为博士生导师,且著作多多,但平易近人,言谈随和,甚至还有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童趣。尽管多年来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钩沉,但他不随俗流,不人云亦云,而是以独特的视角,在多个历史视点上,勇于探索,自成一家之言。更可贵的是,已是名人的他,在说起成长的历程时,却不饰不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朱子彦,也让我们从中参悟出了一条励志育人之道。
从“休学”中奋起
家境颇好的朱子彦并不快乐。 5岁那年,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发病时,气喘憋得脸发紫,唯有送医院去接氧气、吊“肾上腺素”点滴,他才能平哮止喘。
时常发作的哮喘,令正在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读书的朱子彦苦不堪言。那时,济济一堂的学子正在专心致志地聆听老师的讲课,他却因气涌喉痒而咳喘不止,由此打断了老师的授课,也破坏了同学的学习兴致。班主任老师不得不建议他休学。无可奈何之下,他休学回家。
休学的少年朱子彦曾经有过一段苦闷与彷徨。是啊,看着同年的孩子背着书包,唱着跳着去上学,他却只能扒着窗口看淮海路上的街景。好在朱子彦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乐园,那就是他拥有一部自小就情有独钟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半文半白的小说对于一个才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是很大的。怎么办?这时,曾在江苏南通女子中学读过高中的母亲王景文,就成了他的文言文启蒙老师。母亲非但给他讲解《三国演义》里出现的文言文,还到卢湾区图书馆去借一些优秀的古典散文读给他听。日积月累,朱子彦非但将一部《三国演义》读得滚瓜烂熟,而且还通读了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及“二十四史演义”。
每天除了读史,母亲还要求儿子按照学校教学的进度,自学小学课文。通过自学和读史,他以全科优秀的成绩获得小学毕业证书,与原来的同学一起升入建庆中学。
初中刚毕业那年,恰逢“文革”。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想读书的朱子彦无学可上。以后他被分配进了闵行的一家大型国营电机厂工作。然而,没等他高兴一个星期,人家说他有肺气肿,居然取消了进工矿的资格,而被分配到街道一家电珠加工场里打杂工。朱子彦的情绪一落千丈。
街道工场的氛围和社会上无休止的“革命行动”,都令朱子彦感到日子难过。怎么办?他暗下决心,坚持自学,让学习去冲淡郁闷之情。于是,人家天天敲锣打鼓喊口号、挥红旗闹革命,他就到处想办法去找书看。那时,他有一位朋友家里的藏书颇丰,又因为“出身好”而未遭造反派的破坏。朱子彦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就找上门去借书。那位朋友说,在我家里看,可以;想借回去,不行。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里,万一这些书被造反派发现,那是要遭殃的!朱子彦表示同意,从此他就成了那位朋友家的常客。在那个小天地里,坐拥书城的朱子彦如入山探宝,如下海采珠,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这时,他的读书兴趣已从读故事性的“演义”,向正史《三国志》、《中国通史》,以及《文心雕龙》、《艺概》等文艺理论过渡,他还读秦牧、杨朔、刘白羽等散文大家的美文。当然,他也读了不少马、恩、列,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学海无涯,知识真是个深不可测的海洋。
朱子彦是个喜欢买书的人。那时,只要看到新华书店里有他喜爱的书,那是一定要买的。尽管那时,他在街道工场一天只拿七毛钱,可是好书不能错过,于是只好节衣缩食,省下钱去买书。那时,他觉得少吃一只好小菜,少穿一件新衣裳都不要紧,只要有好书在手,他就心满意足了。“文革”后期,有一次他去北京,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里看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古书,欣喜不已,就竭尽所能买了下来,结果,连回上海的车票也是北京的大哥给买的。回来后,朱子彦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系统、完整地将这“前四史”通读了一遍。
于是,分配工作的不顺当与郁闷,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读书使朱子彦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日子过得很充实。
有意思的是,街道的干部不知怎地知道了朱子彦是个“蛮有知识的人”,就让他参加“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朱子彦的数理化不大灵光,但文章写得蛮有味道。当他的一篇篇文章写出来后,大家说“瞎灵(沪方言,极好)”!从此,文章写得“瞎灵”的朱子彦就经常被人请去做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的辅导报告,作演讲。从此,文章写得“瞎灵”、口才也“瞎灵”的朱子彦可以不去街道工场打杂,可以很风光地去当辅导老师,当演讲员。
朱子彦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我之所以能没有迷失方向,这与我把握自己,坚持学习,是有很大关联的。这也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
以优秀成绩考进复旦大学
1978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上大学是朱子彦梦寐以求的事,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然而,光有热情是不行的,因为要走进高等学府,就必须参加高考,那种“交白卷的大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朱子彦只不过是个初中底子的人哎!想考大学?他想了想,语文没问题,政治也不在话下,历史更不用说,但数学呢?难,太难了!自小就对数学“感冒”的他,此科成绩一向不大灵光。怎么办?恶补!朱子彦立即向邻居读初中、高中的学生借书,借习题集,埋头学习,埋头做习题。之后,他又去请教在华东理工大学任教授的二哥。哥哥知道弟弟想上大学的心事,就耐心地从一元一次方程到函数,帮助他进入数学的领地。尽管如此,这年考试他还是因为数学太差,而使总成绩差几分而名落孙山。
这个打击令朱子彦醒悟:知识不是靠“恶补”于一时就能真正学到手的,它必须在勤奋之中循序渐进。
高考落第,朱子彦并未意志消沉,相反更激起了踏踏实实学知识的决心。在新的一年里,他认认真真地、系统地再学习,1979年,朱子彦终于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朱子彦是个“不安分”的学生。他在故纸堆里钩沉历史时,时有奇想,闪出思想火花。他总是要提出一些“奇谈怪论”。其中,大胆地对历史人物进行质疑,就令一些同学,甚至老师感到匪夷所思。比如,他对人们对中国皇帝制度的产生与认知的一些定论,就表示存疑;对我国历代的后宫状况,也觉得心有疑窦;至于对《三国演义》中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以及司马昭的历来定论,都觉得有可以商榷之处。尤其是那句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似乎司马昭成了阴谋家的代名词,更有不同看法。其实,唯因司马昭的“三家归晋”,才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战乱之祸,这于国于民都是幸事,比诸曹操的统一北方,更是居功至伟,何阴谋家可言?
于是,他就拿起笔,运用自己多年来的学识积淀和考据,直抒胸臆,写出了一篇篇论文。其中,《论明代的仁、宣之治》,是他毕业时的扛鼎之作。这篇论文获得了专家、教授的好评。不久,这篇论文就在国内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学术杂志《史学集刊》上发表,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
说起这篇毕业论文,朱子彦感慨地告诉我说:在复旦历史系就读的日子,是他最好的学习时光。这里非但学习氛围好,而且多有饱学真才之士!其中,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著名的明史专家汤纲,就令他终生难忘。当时,汤教授在看到朱子彦自选的这个课题时,极为赞赏,他觉得这表现了做学问的勇气与胆识。在汤老师的支持、指导下,朱子彦在史学的高峰上不断地攀升。
勇于探索 立言争鸣
一部《三国志》,一部《三国演义》,对于朱子彦来说,早就烂熟于胸。于是,他从考据入手,写出了《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等。那时,国内还没有掀起“三国热”。
朱子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研究历史,并非只在一亩地里刨食吃。他以多年来积淀下的史学知识,多点式、多视角地去看待中国史,言人所未言之言,著人所未论之论。由此,他在史学界一向很热的“党争”问题上,进行探讨,写出了明史的《胡蓝之狱辨析》、《明代内阁与党争》、《明代“大礼仪”中的党争》、《朋党政治研究》,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他还对中国历代后宫进行了研究,著作了《后宫制度研究》一书;与徐连达教授合著了《中国皇帝制度》。
说起《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一书的出版,还引出了一场风波。那是因为朱子彦对诸葛亮、司马昭等三国历史人物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评价,没想到,书一出版,就遭到“网民”的攻讦、谩骂。对此,朱子彦宽厚地说,学术上的事,允许争论,允许有不同见地,这是好事。人家越是骂你,你就越是要冷静地反思,找出更符合科学精神的论点去回应,以理服人。
2007年,朱子彦在多年研究三国史的基础上,推出了其通俗性史论新著《朱子彦论三国谋略》一书,并应邀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中,走马三国,纵横汉魏,侃侃而谈,受到了观众的认可与赞扬,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
朱子彦自198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到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来,他在典籍浩繁的史海里探索,独辟新径,走过了不寻常的治学之路。为此,他付出了超常的艰辛。他说,古人曾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的名句,人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朱子彦不善应酬,但却合群。他说,我是与这个时代一起走过坎坷的人,尤其是亲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历史,见证了这一段值得研究和大书特书的新时代。我作为一个在魏晋史、明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史学领域里从事史学研究者,有责任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章。
在采访结束时,朱子彦教授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我想借《大江南北》一角,寄语青年一代,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一定要用勤奋、坚持的精神,耐得住寂寞,去学好、钻研好你所选择的学科,创造性地、科学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开创一片新的天地,做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