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期●文化战士天地●
富华∶传奇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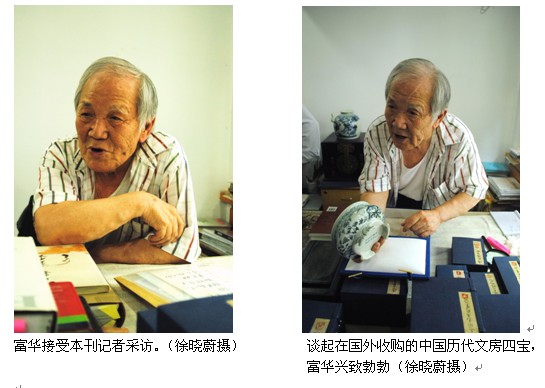

2011年国庆前夕,上海的行道树绿叶染黄,预示着又一个秋实累累的丰收季节到来。这天,我们来到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著名画家、新四军老战士富华的家。他去年春天从英国回来,暂住在上海西区租借的房子里。
一走进富老的家门,立即被室内陈设的刀枪剑戟所吸引。我们知道,他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家庭,是正蓝旗、富察氏的后裔,祖父、父亲都有一身好武艺,因此他自幼得到真传。他的书房墙上挂着由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手书的“红雨楼”镜匾,见证着他俩的深厚友谊。
《大江南北》杂志曾两次刊登庄辛、代琇撰写的文章,介绍富华的传奇人生,引起很多读者关注。老画家得知我们想了解他的近况,非常坦诚、热情地作了详细介绍。
革命情结永铭心头
今年4月份,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东方艺术院与闸北区革命史料陈列馆联合为富老举办个人画展。“有一个叫陈冠宁的人,来到了我的面前”,富老说,“我仔细端详了半天,怎么也想不起此人是谁。”后经张辉馆长介绍,他是陈默(原名陈尔晋)烈士的遗孤。父亲牺牲时,这孩子才11个月。“我几乎惊叫起来,陈默的名字60多年来,一直在我心中萦绕,不断地撞击着我的心。在我86岁时,烈士的遗孤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富老饱含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解放前夕与陈默烈士共囚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的短暂交往。陈默从被关进看守所直至牺牲,不会超过两个星期,时间应该是1949年4月底到5月7日之前。“他被关在1号牢房,与李静安(化名李白)、秦鸿钧关在一起。1号牢房当时关的都是要犯、主犯,所以被称为死牢,只见过其他牢房的人被转到1号牢房关押,从未见有1号牢房犯人转押到其他牢房。因此,只要进1号牢房就必死无疑,至于什么时候执行,里面其他牢房的犯人根本看不见。”
富老回忆着:“陈默在我的印象里,个子比我高,大概有1米70左右,年龄40多岁。从他敏捷的行动,有神的眼睛,强健的体魄,高傲的神气,以及双脚上戴着脚镣,就知道他是非同一般的犯人。要知道即便是要犯李白、秦鸿钧直到牺牲前都未戴过脚镣。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次趁着放风我特意到1号牢房的走廊与他有过一次对话,我低声问他‘你是什么案子’,他警觉地将我上下打量后,用无所畏惧的语气答了一句‘他们谁也不能审我’。仅此一句话,我就明白了这是一位更高层的政治要犯,我们是同志!李白、秦鸿钧等是5月7日牺牲的,在他们牺牲前,我就没有再见到陈默,估计也就在那几天英勇就义了。”
这时富老有些哽咽。听着他娓娓道来,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上海解放前夕的腥风血雨。稍事停顿,富老又对我们说,最近他做了一件与革命历史有关的事:因为年代久远,许多人都已故去,当年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关押革命者的牢房分布情况已无人知晓,他凭着记忆把一张示意图画出来了。我们非常惊讶耄耋之年的他有如此的记忆力,问这是否与作为美术家的观察力有关,而富华说:“这还是在当年搞党的地下工作时练就的本事。”
1943年,17岁的他为抗日救国而参加革命,曾在苏北加入新四军,1945年调至华中局敌工部任副部长,同时是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通信员兼秘书。次年2月,由陈修良主持支部大会,为富华举行了入党仪式。他与陈修良化装成母子,潜伏在南京,陈修良在南京中华门外开五金店作掩护,富华在中华门外赵家岗小学任校长,兼任中学区总支组织委员,从事学生运动。他告诉我们:“那时与这些中学地下党组织联系,向他们布置工作或听他们汇报工作,都是口头的,因为怕暴露,很少用书面联系,全凭记忆。”1947年年底,他在上海北郊大场地区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幸于1949年1月13日被捕,关押在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直至5月23日成功越狱。富老说:“我一直利用放风的机会,仔细观察牢房的每个角落,时刻都在琢磨着如何逃出去,所以我今天就能绘出这张示意图。”
富华的革命经历,使他有永不泯灭的情结,这也反映在他的国画创作中。我们对《井冈星火》、《圆圆鸡蛋吃个饱》、《战地黄花》等几幅画作十分欣赏,问他如何把红色元素融进画里,创作灵感来自何处? 满头银发的富老即兴给我们唱了一首歌:“井冈山,南瓜甜,穿上草鞋下吉安。灯火小,普天照,迎来五洲红旗飘。”我们顿时明白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诗中有画”,他根据井冈山民歌创作了《井冈星火》,又根据陕北民歌创作了《圆圆鸡蛋吃个饱》,表现人民群众慰劳子弟兵的感人情景。《战地黄花》则是毛主席诗意画,考虑到整个画面中都是黄花,似乎显得有些单调,他别出心裁地加了三片红叶,神来之笔跃然纸上,寓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无数人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画这几幅作品,就是要表现‘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这样一个主题,无论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都不能脱离群众、忘记人民!”富华说。
丹青艺术传习海外
1956年春,富华经市委组织部调任,筹办上海中国画院,担任支部书记、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他的老领导、干娘陈修良得知后叮嘱道:“你还很年轻,要好好向画家们学习,努力工作。”就这么一句话,启迪和激励出他这位刻苦学习、勇于创新、硕果累累的画家。1965年,他领头创办上海油画雕塑室;1978年,他和赵丹一起创办了民间性质的海墨画社。
富老非常激动地拿出一叠稿纸递给我们说:“这是我1998年初在伦敦得知干娘陈修良逝世的噩耗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来的,算是叙事长诗吧。”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他说:“我就想在自己心里留个念想,发不发表这都不重要。”说到这里,富老的眼角湿润了,此时又勾起了他的回忆,当年与陈修良夜宿洪泽湖西岸菱塘桥、潜行到南京,一路上不止一次碰上敌特,与其斗智斗勇,最后化险为夷。他们那种出生入死、情同母子的真挚感情,深深地埋在富华的心底,同时也深深感染了我们。
1985年,富华离休。第二年,不安分的他走出国门,远赴英国,他要看看老外到底能不能接受中国传统绘画,水墨丹青在海外的地位究竟如何。他在那里举目无亲,连26个英文字母都念不全,更别提用英语会话了,但他凭一支毛笔,以画会友,结识了许多英国朋友,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帮助。富华以弘扬中国传统艺术为目的,无论是讲学、授艺还是举办画展,每到一处,都不断地向人们介绍中国画。在海外生活这些年,他共举办了30多次画展,在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都留下了令人惊羡的墨迹。
看着堆放在房间里的画作,看着精神矍铄的老画家,我们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富老的画在英国颇受欢迎,那里有一大批喜爱中国传统绘画并且坚持学习、研究、交流的人,聚拢在富华周围的就有七八百人,他们成立研习中国画的社团,定期出版会刊,举办画展。在一次富华的画展上,有位英国老太太每天都来,直到最后一天,她对着一张画哭了,原来她特别喜欢那张画,但经济能力不允许她买下来,富华得知后,便把那幅画送给了她。在海外从艺20多年,富华愈发体会到:越是有中国传统特色、民族特色的艺术,越是会被海外的观众欣赏和喜爱。
“你们来看看我在英国收集的中国历代文房四宝吧!”我们早就注意到,在书房硕大的桌子上放满了深蓝色的盒子,叠了几层高。他小心翼翼地把一只只盒子打开,如数家珍地介绍里面的东西——“东晋青瓷三足大砚”、“唐多足象腿砚”、“宋龙泉大砚”、“明青花两用砚”、“清象牙满雕笔筒”……令我们目不暇接,喟叹不已。
在英国,富老不断地把自己的画卖了,去收购这些流落在外的宝贝,有时卖一幅画的钱还买不来一件,要两三幅才行。富老对我们说:“我把200多件东西带回来,是要给它们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它们应该回归祖国。”我们禁不住问:“难道您想把它们捐了不成?”他肯定地回答:“是的!国内已经没有这么齐全的古代文房四宝了。我已86岁了,自己无所谓了,只要把这些宝贝安顿好,我就放心了!”
我们深为富老高尚的境界感动!作为一位老艺术家,只身在海外奋斗多不容易啊,而他用自己心血之作换回的历代文房四宝,在当今国内艺术品市场准保能卖出天价。可是他却郑重、潇洒地决定捐给国家——“它们属于中国人民”。
富华与“文革”后期结缘的患难妻子陈奇已在2002年分手,而他与他的经纪人、酷爱中国传统艺术的英国老太太端·多乐喜的三年正式婚姻,也因她去年不幸病逝而告结束。富华的青年、中年时代已经足够曲折和传奇,而他的老年岁月似乎注定了还要继续曲折和传奇下去。他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后,还要回到英国去,他在那里还有许多学生,要办许多事情,继续弘扬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富老最后对我们说:“画家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历史,属于现在和未来。他的责任是给人们幸福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