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期●散文●
追寻逝去的空间
作者:武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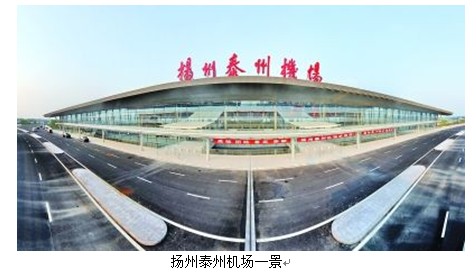
1938年,我还是11岁的孩子。日军侵占了扬州城,一批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小学教师,跑往东乡农村,继续教育事业,坚持抗战。我的寡母崔宗玉,跟随原城北小学校长金声甫一家五口,在麻村、沈家厦、麾村等地因陋就简的小学教书。我跟着母亲,也辗转到过这些村子,极其艰苦的生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久久难忘。如今到了耄耋之年,还想再去看看。2012年12月初,在女儿陪伴下,我来到扬州为母亲扫墓后,又在外甥大力协助下,请到了一位热心的司机,奔驰在东郊的原野上,追寻那70多年前的足迹。
正是晚稻收割的季节,原野上一片金黄。万福桥,是进出扬州必经之路,今昔相同,而对我这老人却大不一样。当年木桥老旧,江水滔滔,独轮小车,吱吱嘎嘎,艰难前行。特别是,经过桥头,还要向岗哨日本兵曲躬“敬礼”,这种屈辱的旧恨,至今仍涌上心头。
扬州乡村现在的道路还算好,白色的和黑色的路面,宽可驶汽车,村村相通。只是没有明显的路标,这就苦了过客,即使是本地的司机,也不可能熟悉每一条乡村小道。我们不停地向路人打听,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目标:麻村。记忆中麻村的“标志性建筑”是村中心一长排砖瓦大屋,朝南有许多大门。房主人是王姓破落地主的大家族,兄弟分家后各享一宅,住在各个大门里,我们就曾借住在“二房”兄弟家中。围绕大屋周边,是许多疏散的独家农户,有草房,也有砖屋。村中心大屋前面有一个水塘,当年人们就在塘边淘米洗菜。我们以为“标志”鲜明,很好找,高兴地进得村来,却不禁大失所望。记忆中的一排大屋荡然无存,面前只是一个密集的居民点,紧挨着的一家家新房,极其陌生。热心的村民听到我提起曾经有个王姓大家族,就找来了一位王家的后裔,40多岁,看来大概是四代以后的人了。他告诉我们,那一排砖瓦大屋,当年颇有名气,人们叫它“十八个大门”,现在已经完全毁塌了。他领我们去看了那一片遗址,面前果然还有一个池塘,现在水已很少,污染严重。残留地基一小部分变成菜园,更大的部分盖上了一座新屋,敲门半天,院内无人。我们只好依依惜别,总算看到了今日的麻村,女儿的照相机里留下了这些印迹。
村民指点麾村就在麻村旁边,车行不远,就到了。记忆中的麾村,首先是我和母亲所借的那间与牛同住一室的草房。当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小学教师薪水本来就很少,而当时国民党游击区政府,连极少的薪水也发不出,母亲常常为无米下锅犯愁。在麻村我们还能借住在砖瓦房里,到了麾村,住的不仅是草房,旁边还有一位邻居——大黄牛。母亲借来几块木板,在另一个角落里,搭了一张“床”。房主说,黄牛很干净,下面铺的稻草也天天换新的。说得不错,这是一头母牛,膘肥体壮,温顺干净,稻草也发出清香。开头我还不习惯,住下来也不当回事了。记忆中还有一件事。那时,我在郭村小学读六年级,平时住在学校,有一个星期天,正好回麾村住在家里,听邻居说来了部队,对老百姓很客气。我好奇跑出去看看,门口就有一个穿军装的“兵”,扛着枪站在路边,见了我也没有查问。我一口气跑到村头,果然看到在远处水稻田的几条田埂上,一支队伍向北行进。村头的打稻场上,散坐着许多“兵”,好像在交谈休息。特别是,旁边架着一挺机关枪,引起了我们几个孩子的兴趣,围着它观看,问这问那。管机关枪的那个“兵”,和过去碰到的“兵”不一样,不但对我们毫不厌烦,还笑嘻嘻地指着零件讲解说明。他们是什么“兵”?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和气?当时也不懂得去询问,更想不到10年之后,我竟然也在另一个地方成了他们的“同志”,走上同一条道路。在麾村的这一场“偶遇”,便是留在我一生中的一个难忘的画面。
车子停在柏油路的十字路口,行人说这就是麾村,看看四周完全不像。我说:“这是新麾村吧,我们要看的是旧麾村。”司机转了一个弯,还是柏油路,看到路旁一位老者在休息。我们下了车,打听“旧麾村”,他说这就是“旧麾村”。老者高寿,也已八十了,是“过来人”,他的话当然不会错了。旁边一个青年好像是他孙子,介绍说,老者是以前的村支部书记,这是一方的“老土地”呀,碰到最好的“访古”对象了。我问起当时一位小学校长好像姓刘,名字忘了,“老土地”马上接着说:“是不是叫刘素秋?”我一听马上对准了“号”。可是他已经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整死了。我又想起他还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刘鸿笔,老书记一听就说熟悉,可是也在几年前去世了。如此人事沧桑,不胜感慨,没有找到当年村头军人们聚集的稻场“遗址”,也没有看到与黄牛为伴的草屋。虽不免遗憾,但是遇到一位老支书谈说往事,也算意外的收获,我们和老支书一起照了相。
车在稻海中转来转去,逢人便问沈家厦,终于问到了。记忆中,母亲在这里教小学,村子里农民很多,也很友好,当年我们借住在一户农民家中,矮小狭窄的土坯草房。旁边却是一座高大的砖瓦庄园,主人姓王,不仅拥有大片土地,而且开了一家榨油厂。人们都说他很有钱,为了防土匪,家里养了保镖,又盖了一个高高的岗楼。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庄前踱来踱去,腰间还挂着一把手枪。听说沈家厦小学就是他家出钱办的,学生很多是姓王的子弟,或是王家的亲戚,没有一个农民子弟。有一次,听说王家请来了一个英语教师,经过母亲的联系,让我也去听课。庄园里面有一个花园,讲课就在花厅里。
下得车来,环顾四周,村子变小了,村民变少了,岗楼没有了,庄园更不见了。热心的村民把我们领到一片废墟,这里还残留着一块没有屋顶的断垣残壁。旁边是一座新瓦房,里面走出来一位中年农民,主动介绍说这里就是当年的王家庄园。看着墙基残留的青砖,大而厚实,和现在的砖块不同,断墙上的一处八角窗的砖砌边框,还留存着一丝庄园往日的风采,这些难得的印迹,大概不久以后也将在空间中消失。几十年中,这位地主兼资本家的庄园主,经历过什么坎坷厄运呢?已经不可考了,中年农民说,前几年,这个家族的后人,回到沈家厦来废墟看望过一次,还向乡亲们分送了一些钱礼。这也不妨说是沈家厦庄园“史诗”的袅袅余韵吧。
1938年的时间虽然消失无踪,但是麻村、麾村、沈家厦的空间,毕竟还留下了一些依稀的印迹,能够追寻到它们,也可算此行不虚了吧。
车出沈家厦,奔向归途。在一片黄色稻海的远方,外甥忽然发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脉现代化的建筑。他惊喜叫道:“这里靠近泰州,那就是机场了。”大家极目望去,果然好像还有一架飞机正从地面飞起。这样,时间就把我们从遥远的、苦难贫穷的20世纪30年代,一下子拉回到现实的、富裕丰乐的21世纪10年代。而地球上扬州东郊的这一块空间,又增添了人类活动的一个崭新的印迹,几十年后它会变成什么样,不妨留待后人来追寻吧。为此,我们又停下车来,拿起照相机,以机场和稻海为背景,和外甥、女儿、司机四个人,一同留下了几个难得的镜头。
上一篇:脊背上的疤痕下一篇:学唱《新四军军歌》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