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期●缅怀篇●
你好,韩慧如校长
作者:张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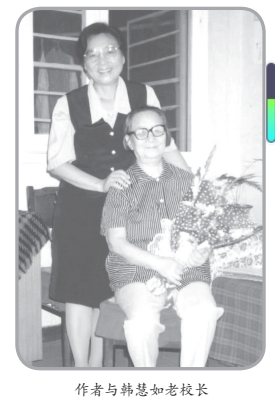
面前放着一本发黄的《我的回忆》,打印于1985年,是韩慧如72岁时写的。当时她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也许就是这次起死回生,让她决心写下在旧社会经历的苦难,以及与丈夫秦鸿钧烈士和战友们千难万险的革命斗争经历。
解放后韩慧如长期担任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1954年我插班到“一中心”的四年级,并在那里毕业。而今重读她的回忆录,我亦年近八旬。她是我今生难忘的一位老师、长辈。韩校长瘦瘦小小,站在人群里看不见。她在大会上从不讲漂亮话,也很少表扬或批评哪个学生,但她却是整个学校的灵魂,无可争议的核心。
崇高风范
1935年,韩校长经由姐姐韩慧英介绍参加革命后,先辅助姐夫陈为人保管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密文件,即“一号机密”。她曾在形势危急时,一个人坐上三轮车把两大箱文件从敌人眼皮底下安全转移。1938年,党组织安排她与丈夫秦鸿钧建立地下电台,向延安发送了大量重要情报。1945年,她又同时担任了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上海即将解放时,电台被发现,夫妻双双被捕受尽酷刑,但没有吐露一丝党的秘密。秦鸿钧在1949年5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韩慧如于5月25日与3位战友成功越狱,迎接了5月27日的上海解放。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上门征询她的工作意愿,其中不乏重要的领导岗位,可她一口就说:“我以前做过教师,我只想做个小学教师。”于是,我们就有了韩校长。
她深爱孩子,始终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无偏废,看到学生经常问:“你在学校快乐吗?在家里高兴吗?”我们这茬同学是最大的受益者。课堂上每个人都有发言的积极性,课余更有根据自己特长选择兴趣小组的广阔空间,戏剧、合唱、舞蹈、木偶、美术、手工不一而足。这使“一中心”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和音乐特色,从这里走出了笛子大师陆春龄、扬琴演奏家丁言仪,走出了在市里区里屡屡获奖的合唱队……
“文革”时期,韩校长被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以至戴铐坐牢。许多老师都记得,韩校长出狱后被勒令打扫学校卫生和厕所,每天弯着瘦小的身躯擦洗,感觉“惨不忍睹”。可她却说,我擦干净了,孩子就会舒服。她每天一遍遍擦马桶,冲粪便,扫地面。全校公认:韩校长打扫期间,是学校厕所最干净的时期。
满门忠烈
1956年我小学毕业后,直到1962年去安徽务农,再到1993年回沪工作,都与韩校长保持联系。尤其定居上海后,我更加了解到她的每个家人都是一部书,最鲜明的共性是忠诚、骨头硬和无私奉献。韩校长的爱人秦鸿钧烈士,1927年入党,1936年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学报务,没经费没交通,只有一张从东北走小道进苏联的手绘地图。他每天夜行,穿森林、爬高山、蹚河水、避野兽,走了好几个夜晚终于越过国境。
在苏联,秦鸿钧以小学四年级的文化起步,学俄语、学报务、学修理电台设备,为了能早日回国执行任务,日夜拼命苦学,居然在半年里能够独立操作和翻译电码。从1937年到1949年,他在上海想方设法躲避敌人的追查,向党中央发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了掩盖光线和敲键声,他每搬一次家都用纸、布把门窗和墙壁糊得严严实实。由于长期闷在斗室通宵发报,以至满口溃疡,双腿站不起来,而桌椅和地面都是汗水。
1949年3月电台暴露,秦鸿钧夫妇和同做情报工作的张困斋(张承宗的弟弟)被捕,受尽酷刑。有时,敌人还让他们相互看对方受刑,并故意在他们面前把来探监的一双小儿女推赶出去,让他们听到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喊“爸爸!妈妈!”但无论敌人使出什么花招,他们都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5月7日,韩校长眼睁睁地看着秦鸿钧和张困斋被五花大绑押上汽车,知道永别时刻到了,悲痛欲绝,但狱中党组织“准备牺牲、争取越狱”的指示和丈夫的遗言让她冷静下来。5月25日,她趁敌人惶恐不安、疏于管理之时,与缪剑秋等3位战友机智越狱,受到一对普通市民姐妹热情帮助,在她们家隐居两天,终于等到了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韩校长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受到毛主席接见。离休以后,她致力于关心下一代工作,2000年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直到2009年去世,她一天也没脱离革命工作,并要求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红十字会作医学研究。她说:“国家为我治病花了许多钱,我的遗体只能作一点点补偿。”
韩校长家最小的孩子是儿子秦裕民,乳名“小小”,父母被捕时只有9岁,跟着姐姐颠沛流离。解放后,裕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安交大无线电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脑工程师,参与“银河”巨型计算机研发。他曾带8名同事去美国参加培训,国家发给每人每天35美元生活费。当时外汇紧缺,秦裕民提倡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他们省吃俭用,竟省下来一半、5000美元上缴国家。
后来,秦裕民担任锦江集团电脑中心主任,决心研制适合国情的酒店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为此殚精竭虑,耗费巨大心血,终于研发成功,使上海的酒店业第一个实现了与世界旅游业接轨。但他也积劳成疾,1990年倒在了50岁的门槛上。当时,他的儿子秦岭也只有9岁,与秦鸿钧牺牲时秦裕民的年龄一样。1993年我回沪工作后到韩校长家里,看到东西两面墙上各挂着秦氏父子的黑框黑白大照片,一样的浓眉英俊,一样的坚毅眼神,默默相对。我受到强烈震撼,一时哽咽。
韩校长与秦鸿钧的女儿秦裕容,乳名“咪咪”,父母被捕时11岁。解放以后,裕容发奋学习报效国家,在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为返回式卫星和神舟飞船的研制立下汗马功劳。她获得2000年国防科技三等奖,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母女同获这一殊荣,实属少见。她也和母亲一样,很少谈自己。我是从王蕙炎老师那里,才知道裕容在北大念书时,有次周恩来总理请她和几位烈士子女到西花厅的家里过节,和他们谈到深夜,邓大姐(颖超)说,太晚了,孩子们就在这住下吧。那一夜,裕容感受特别温暖,可她从不炫耀这事。
2017年,我接到裕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韧,我的记忆很差了,感觉不太好,我要去住养老院,跟你说一下。”此后我多次去电话,没人接,心中不安。果然,她的亲人证实,她后来失忆了。痛心啊!
晚年著书
2008年初,韩校长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书《真正的共产党人》。促成她下决心出书的,是齐心同志(习仲勋夫人)的亲笔信,信中明确希望她出书:“你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让人知道过去是很必要的……后代需要这样的精神财富,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要作为传统教育代代相传。” 韩慧如将出这本书作为党的任务在病中坚持,王蕙炎老师也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王老师是位1948年就参加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按韩校长的口述写出了7万字的《我的回忆》初稿,后来又从内容、结构、字句上逐一补充调整核对修缮,最终完成了10万字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书稿。王老师交待我任务:尽快实现出版。2007年,我找到时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陈和,他连连说:“这是好事,好事!”当年即付印,让韩校长亲眼看到了这本书。这本书于2010年再次加印并补充了秦裕容的回忆文章。
2021年春,王蕙炎老师去世,和韩校长又并肩战斗在了另一个世界里。
曾经,我觉得《真正的共产党人》书名过于平淡,不能吸引人。但当我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一些共产党员丢掉了信仰,一些党的干部忘记了初心,腐败堕落,甚至叛党卖国。对比韩慧如校长和王蕙炎老师这些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在任何环境下都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坚定为党的事业全力以赴、奉献到终老的共产党人,我豁然明白,只有“真正的”才能概括他们彻底的党性和人民性。我完全接受了这个书名!
韩校长,您好,我又想您了。
上一篇:一寸赤心惟报国下一篇:新四军题材:盐城文艺舞台上的主旋律